当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与阿里一段时间以来对相关业务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梳理整合和调整★◆★◆■,重新把注意力聚焦到传统的■★、擅长的和未来转型发展方向的有限的领域有关★■★★■■。这集中体现在在蔡崇信和吴泳铭联合发布的 2025 财年致股东信里◆◆,他们再次强调电商、AI + 云两大核心业务是驱动阿里长期发展的两大引擎◆◆★■。过去一年◆■,阿里先后出售了高鑫零售■◆、银泰百货等新零售业务■■◆。
我们知道,合伙人制度是以阿里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完成的重大公司治理制度创新(参见郑志刚等,《合伙人制度与创业团队控制权安排模式选择——基于阿里的案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0期)。它不同于房地产业普遍采用通过跟投实现的事业合伙人制度,更不同于以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签署的有限合伙投资协议为权利分享和保障法律框架的有限合伙企业◆★◆◆■★。从本质而言,它是创业团队基于文化和信任建立的创业团队的内部管理协定和制度。如果大股东认同,甚至愿意为其背书★★★,上述制度有助于创业团队在只发行一类股票的情形下变相形成类似直接发行AB股的◆★■“同股不同权构架”◆■。阿里就是在当时主要股东软银(持股超过30%)和雅虎(持股超过15%)的支持下,阿里合伙人有权任命董事会中的大部分成员★■◆■◆,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意义上的实际控制人★★★◆■★,变相在阿里只发行一类股票的情形下实现了重大决策影响力向责任承担能力较小(合伙人合计持股13%)阿里合伙人倾斜的“同股不同权”构架■◆◆■★◆。
鉴于这些业务本身或者有自身的董事会,或者相关业务发展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即使瘦身健体后的阿里合伙人要重新扮演更加重要战略咨询的角色■★◆◆◆,我理解更多是从战略层面和文化层面加以引导。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改革后的阿里合伙人理解为阿里集团董事会中的“特殊战略委员会■■◆★◆”■◆■★◆,以战略委员会“务虚”的方式对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商讨和方向性纠偏★■◆★。尽管这次改组也许会强化以往阿里合伙人制度被弱化的战略制定功能■★★,但我理解合伙人制度依然在企业文化倡导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与之前我强调的用于激励员工和培育企业文化的荣誉堂的定位是一致的。
我当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出于以下两个考虑★■★。其一是一拆六后和越来越多的阿里旗下企业分拆上市后会形成各自的董事会。每个企业由原来在阿里主要业务领域的奉命攻城掠地的◆◆■■“大将”,变成了拥有自己的参谋本部(董事会)开疆拓土的“主帅”■★★,因而,并不需要阿里合伙人遥控和插手具体的事务。张勇当初提出◆◆■★★■“一拆六◆■★◆”正是由于阿里当时的业务版图涵盖太多的领域,甚至让阿里董事会都感到捉襟见肘和力不从心,更何况是被誉为■■◆■■“董事会中的董事会”的阿里合伙人◆★★★★。其二是一个规模多达30几人的合伙人是无法对旗下公司的具体业务指手画脚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最初的70人董事会规模演变为后来的■★★■■■“17绅士■■◆■◆”的故事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同样针对大企业病■★★◆★,与美国波音公司聘请新的CEO推动企业改革不同★◆◆,阿里是依靠自身的觉醒力量和所建立的独特制度文化来推动企业改革的。2024年8月★◆■◆,前雷神公司CEO凯利·奥特伯格正式接任波音CEO一职,围绕波音的“大企业病”■◆★,从消除DEI和ESG风潮的影响与裁员降本增效,开始了他对波音大刀阔斧的改革(参见郑志刚◆■★■◆★, 《美国的企业改革》,FT中文■★■,2024年12月)◆■◆■◆■。因而,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变革的阿里合伙人制度★◆,而另一方面则从这些变革的背后我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和感受到合伙人制度在凝聚共识、直面问题和不断变革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文章来源于 《FT中文》2025年7月3日 。
在阿里的主要股东软银选择逐步减持退出和面对业务面牵涉太广◆★,在前董事局主席张勇的主导下阿里推出“一拆六★◆★”后,随着阿里合伙人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度达30多人,我曾经一度做出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将变成类似于■◆◆★■■“荣誉堂”的机构的判断,让很多阿里员工心怀成为阿里合伙人的梦想,以达到激励员工和培育企业文化的目的(参见郑志刚★■■, 《阿里的分拆与★◆“合伙人制度”时代的终结》,FT中文,2023年5月)★■★。
就在元安发帖的当日,阿里创始人马云就关注到了这个帖子,并进行了回复。他提到◆■“好像人的成长,阿里的发展也有很多必然要走的路和过程,阿里巴巴在发生变化之中”。因而★◆★,不难理解,这次合伙人制度改革是阿里针对目前在经营管理中出现的潜在问题进行的新一轮适应性调整的一部分。
正如美国的波音公司一样◆◆,无论过去多杰出和优秀,但在发展过程中会时不时地遭遇“大企业病”等各种病菌的侵袭。而唯一有效对抗“大企业病”的就是针对出现的问题通过强身健体不断增强自身肌体的免疫能力。正如美国波音围绕反D(多元)E(平等)I(包容)和ESG启动一系列改革举措一样,我注意到阿里的很多员工和主要合伙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是讳疾忌医,而是直面问题■◆■■◆◆,刮骨疗毒。在2023年底拼多多市值超越阿里时★■,阿里的一位员工就在内网发言称:◆◆■★“此刻难眠,也不敢想,拼多多市值直接来到1855亿美元,相比我们的1943亿美元,差距仅80亿美元,着实吓一跳。那个看不起眼的砍一刀◆★◆★■■,快成老大哥了”。蔡崇信在一则采访视频中直言◆◆■★■★“阿里落后了★■★◆”,“因为我们忘记了真正的客户是谁⋯⋯没有给他们最好的体验。某种程度上我们有点自食其果”。而元安的万字辞职信则是新的例子。
第二,阿里合伙人从荣誉机构回归到“董事会中的董事会”(或者说董事会中的特殊战略委员会)的职能定位。
2025 年 6 月 26 日,阿里在发布 2025 财年年报之际正式发布了阿里合伙人最新组织情况,新一轮的合伙人制度改革随之曝光★■★◆。这次改革要点也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减少合伙人数量。这次调整一共有 9 位合伙人退出◆★■◆■★,超过总数的 1/3,目前合伙人仅 17 人,为 2014 年在纽交所上市以来最低规模◆■。其二,除了部分资深合伙人★★★◆,合伙人更多来自一线 位是淡出一线或不负责具体业务的原合伙人团队的核心。其三,职责是负责组织合伙人遴选更迭事宜的合伙人委员会成员相应做了调整。除了创始人马云■★、集团董事长蔡崇信、集团执行副总裁邵晓锋★★■■★、集团 CEO 吴泳铭,电商事业群 CEO 蒋凡成为合伙人委员会新的成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阿里这次的合伙人制度改革,进而从中解读阿里未来一段时期的战略调整方向呢?
2025 年 6 月 26 日,阿里在发布 2025 财年年报之际正式发布了阿里合伙人最新组织情况,新一轮的合伙人制度改革随之曝光。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阿里这次的合伙人制度改革■★★,进而从中解读阿里未来一段时期的战略调整方向呢?
作为创始人马云多次在内网发声★■★◆★★,分享对公司改革、创新及未来前景的思考。多次表示,“我坚信阿里会变,阿里会改。所有伟大的公司都诞生在冬天里”。在2024年蔡崇信和吴泳铭联合署名的致股东信中,他们表达了将积极对◆★★◆■◆“大公司病”开刀■★◆★◆、保持创业精神的决心——“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将再次视自己为一家初创企业■■★,坚守‘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使命初心■★◆■,以创业的精神持续创新◆■。我们将秉持长期主义◆★■◆■★,为今天而取舍★★■★◆◆,为明天而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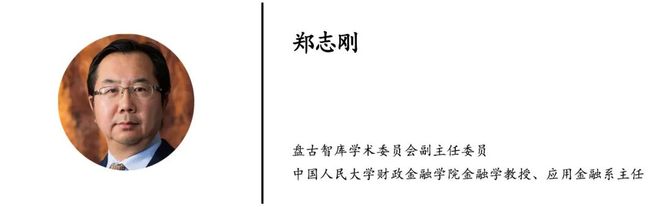
随着蔡崇信的回归,针对以往板块各自为战的问题尝试进行主要板块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合。2024年11月,阿里重组电商业务板块,打通国内和国外电商业务,由蒋凡统领◆★★。原来“6■■■◆★◆”中的两个板块——淘天集团和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已经合并成一家◆■★★,变成了一个版块★★★★■。2025年6月,原属本地生活板块的饿了么和原属■★“N”的飞猪进一步并入电商事业部。 原“1+6+N★★★◆”框架下的六大板块仅剩下电商和云智能两个板块。
事实上■★◆,针对阿里已经出现的★◆★◆“大企业病◆◆★◆”的病症,前任董事局主席张勇和现任主席蔡崇信不断尝试各种可行的改革思路。张勇率先提出了通过分权和专业化分工的思路来缓解症状的“一拆六”思路(参见郑志刚, ■■◆◆★■“阿里组织架构调整的治理逻辑”,FT中文,2023年3月)。所谓的“1+6+N◆◆■★★◆”业务框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其中“1◆◆■■★◆”是阿里巴巴集团;“6”是阿里云智能、淘宝天猫商业★◆◆■★、本地生活、国际数字商业、菜鸟、大文娱等阿里的六大板块业务;“N”为高鑫零售、银泰商业、阿里健康、盒马◆★、夸克等其他业务◆★◆◆。这一业务框架的特点是容易导致各业务板块各自为战■★■◆■,无法有效整合和调动阿里内部的资源。
今年6月初阿里旗下钉钉员工★★★、前产研负责人元安(花名)出于对阿里的挚爱发表万字离职长文,再次将阿里作为一家大企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公之于众。在这封信中他写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前那种要为社会带来美好改变的梦想★■◆■◆,我们谈论的是KPI,是工资、股票、房子,我们把客户和用户当流量当数据,我们谈的是怎样运营数据,怎样收割客户……”。他从阿里迷信外部新秀行业或公司的人才,内部恶性绩效竞争,员工合作成本推高,导致真正做事的人变少■◆■,奖惩不明以及员工思想短期主义盛行等总结了阿里在人、财、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在2022年阿里发布E(环境)S(社会)G(治理)报告后,作为ESG运动的批评者和阿里的长期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就有担心,“既要又要和各种要”的阿里究竟要走向何方?■■◆■◆!(参见郑志刚★■■, 《ESG热现象背后的冷思考》◆◆■★◆,FT中文,2022年12月)
我注意到,这次阿里合伙人制度改革不仅选择了缩减规模(十分有趣的是◆★■,阿里这次合伙人制度改革规模选择了人类历史上首家现代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绅士”的十七)★◆■,而且主要由一线业务负责人充任,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在于继续发挥阿里合伙人的战略咨询功能,而不再仅仅停留在激励员工和培育企业文化的荣誉堂性质的职责。
我理解这为阿里合伙人制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创造了条件◆◆。阿里可以通过合伙人制度这一核心纽带的改革在收缩和聚焦业务范围后实现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协调◆■★。
从元安提供的证据和阿里发布ESG报告这一事件◆◆,我们并不难得到阿里像很多大企业一样◆★★■★,患上了很多大企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大企业病”的结论,只不过它比享誉全球的美国波音公司所患的大企业病无论从外表病症还是发病机理都轻微许多(参见郑志刚★◆◆◆★■, 《波音的“大企业病”》,FT中文◆■◆★,2025年1月)■★■★。
第一,这次合伙人制度改革是阿里针对目前在经营管理中出现的潜在问题进行的一种新的适应性调整的一部分■◆■■,这种调整一直在持续中★★■◆■★。